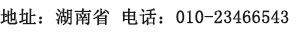今天是年4月12日,星期二,广州天气多云。全文约字,阅读需要5分钟左右。最近广州疫情防控形势有点严峻,希望看到这里的你,可以做好个人防护,勤洗手,祝你健康平安。
最近在看一部年的台剧《一把青》,里面有一个片段是邵墨婷朗读韩愈的《祭十二郎文》,潸然泪下。邵墨婷说,她那个年代的国文课本,有很多人过世,很多祭文,祭文把过世的人,描写得很完美。她认识的江叔不完美,和身边的亲人、朋友,还有去了美国的小朱青阿姨一样,很多缺点,所以课本上,不会记载他们。
这篇小作文,只是简单的记录一些,我还记得的人,不在的,还在的,那些人。
阿公年12月22日,冬至,我妈的父亲,95岁,病卒。估计是懂了,也回去了,看到了,所以才记得这么清晰。我家在湛江吴川的一个小村子里,我小的时候,不知道外公、外婆这样的称呼以及意义,只知道我妈的父亲母亲,在我们村那边,叫做“阿公”“阿婆”。
那天是星期日,我和我哥晚上的车回去,周一早上再过去舅家的。那会阿公还没有下葬,我们过去的时候小姨在门外面,她叫我进去看看。我有点害怕,懂事以后还没有经历过,但我知道我应该进去。阿公睡在舅家的大厅里,身子下是一张竹席,盖在身子上的也是一张竹席。竹席间的阿公瘦瘦的,没有生气,真的只剩下一副躯壳而已了。阿公身边是我妈、大姨、二姨。没多久,阿公入棺了,棺内一个人,棺外很多人。
入棺、火化、下葬。阿公出去的时候,那一程我只是送了一段路,送完那一程的人回来后,我看到了两张纸,忘记名字了,一张关于火化的,一张关于死亡证明的。阿公,走到最后,关于他自己,只剩下两张纸。
那年年中的节假日放假,我回家,我姐和我去看过他一次。那会,阿公已经走不了了,卧病在床。我们去到的时候,阿公依靠在二姨身上,一样的不知道我们是谁。
我的记忆里,阿公脾气很不好。在我小的时候,有一年春节,他要打阿婆,阿婆躲在三舅房间的衣柜里。有时候,他会在家门口那边敲这个敲那个,会吵到别人,有人说他,他也脾气不好。有时候,他会去市场,偶尔会有人向舅那边投诉,他们会把他回来。
我的记忆里,阿公很客气。阿婆不在以后,阿公中午有时候会走来我家,我姐那会在家,会问他吃饭没有,给他盛粥,坐在饭桌上吃。阿公听力不好,每次问他话,都要比平常说话大声点。阿公吃完,会放钱在桌上或者给我的小外甥,有时十块,有时五六块,有时两三块,他好像是来下馆子的,不是来女儿家。
我的记忆里,在我们家的人中,阿公好像不知道我们是谁,只知道我妈还有我爸。阿公看我们,很陌生,我们看到他,要跟他说我们是谁。每次来我家,看不到我爸妈的话,都只问他们去哪了。不知道是因为年纪大了,记性不好了,还是因为我们只是逢年过节才出现在阿公视线里,时间短到阿公记不得我们。
我小的时候在阿公阿婆家,但我小时候的记忆里没有阿公这个人。第一次的记忆,是阿公要打阿婆,但脑子里没有这个人的样子,只有“阿公”这个名字。到后面阿婆走了以后,阿公时常来我家,才慢慢有了一些关于他的记忆。现在,也只剩下这些了。
阿婆年,不记得是夏天还是秋天,我妈的母亲,75岁,病卒。那个时候,我还在上初中,住宿,没有回来。时间太久,我都忘了,忘了我为什么没有回来,阿婆的样子,我也快记不得了。只记得,我周末回来的时候,阿婆已经不在了。
我小的时候,是在阿婆家长大的,至于是多小的时候开始,我不记得,大概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,我回家住了。我妈老是说,我小时候没人管,天还没亮,她就放我在邻居家,待在灶台旁,看着那家老人煮粥,煮完了天就亮了,我就自己跑去阿婆家了。
以前,阿婆还住在老房子里,印象中,那个房子有个天井,天井下有一棵茶树,天井的四边有四个房间,阿婆住在西南方向的一个房间里,只有一张床。有时候,大姨的大女儿也会来,我们三个睡在一起,我睡中间,但是她常欺负我,阿婆会把我换出来,让我睡在外面,阿婆在中间隔着。
以前村里很多老人都会织丝网,白色的,很长很长,织完了可以卷成一把,拿去卖。阿婆也会织,把网头绑在木高脚凳上,然后白天空闲的时候,把凳子、椅子搬到小门口,借着光,左手稳住小小木棍,右手一上一下地在那些白色小网口上穿梭。我不出去玩的时候,会搬个凳子,坐在旁边,帮忙入丝。以前不懂,那些网是用来做什么用的,后来小学以后,认识了同学,知道了离我们村远一点的地方,有海,那里有鱼,这些网可以用来网鱼。阿婆还会晒咸鱼,把鱼杀干净,放在竹筛上,晒着。有时候,那些鱼干晒着晒着,会有白色的小虫,总是成群结队出现的。阿婆会用牙签把它们挑出来弄掉,我觉得有趣,也跟着这样做。
手织的细渔网就是这个样子后来,阿婆搬到了隔离的房子,原来的老房子只有阿公在住了。那个房子三个房间,阿婆住在西边的房间,有两张床,搬去那里以后,我好像就没有和阿婆睡在一起了。
在我们村,煮饭的地方,以前几乎没有人说“厨房”,我们叫“火炉”。灶台里,有时候烧的是木柴,有时候是晒干的禾秆,有时候是松木丝,这个要看锅里煮的是什么好吃的。新房子的火炉,样子和老房子差不多,都是小小的,由一些砖头简单地堆砌起来。新火炉旧火炉,过的都是一样的日子。阿婆自己煮饭,我不出去玩的时候,会在灶台旁帮忙看着火。有时候,禾秆里会有一些还没有掉落的稻谷,进火里一烫,就膨胀蹦开了,外面那层*衣变小了,稻谷变成了大白胖子。阿婆说那些可以吃,所以第一次看到蹦出到灶台口的大白时,我就捡起来,吹一口,再小吃一口试试,边缘是脆脆的。于是,后面再到火炉灶台看火时,就把带稻谷的禾秆放在一起,一点一点地放到灶台口,生怕太进去了,稻谷爆了捡不到。
新房子的火炉旁还有一块地,阿婆会在那个空地上种一些吃的。在那里,我第一次见到挂在枝上的冬瓜、跟着太阳转的向日葵。冬瓜原先是挂在枝头上的,后来慢慢长大了,阿婆就把它们放在棚上,这样大冬瓜就可以越长越大,等它长大到可以吃好几顿的时候,再把它摘下来。还有向日葵,葵籽是阿婆在大姨那里拿的,播下以后,就慢慢长大了,那是很高、很漂亮的一片向日葵,到日落结束的时候,它们就变成了齐刷刷地向着西边的样子,抬头挺胸的。我看着觉得很好看,于是就带了一棵小苗回家,种在家门口的空地上,幻想着它长大的样子,和阿婆种的一样大、一样好看。可是它长不大,还是矮矮的,唯一安慰我的是,它开花了,跟着太阳跑,但是没多久便化作春泥了。那个时候我想不明白,为什么它长不大,现在也还是不明白。可能是我把它种在沙地里,阿婆把它们种在土地里,也可能是我种的是它,阿婆种的是它们,也有可能是我浇的是河水,阿婆浇的是各种各样的水。有很多种可能性,但是我找不到答案。
藤上的冬瓜在我们村,番石榴(学名),我们叫它们“花桃”,高中以前,我并不知道番石榴这个词,现在我见到它们,还是习惯称它们为花桃。还有阳桃(学名),我们叫它们“五敛”,小学课本里有一篇课文,关于杨桃的,书上杨桃的图片,和阿婆家两棵五敛木上的五敛好像,所以知道了五敛还有一个称号,是杨桃。
阿婆家有两棵花桃木、两棵五敛木,每年都结好多果子。我最喜欢在五敛木那里玩,因为两棵树很大,白天爬上去,从这头到那头,然后累了可以坐在树枝上,小腿在那里摇来晃去的,树下面还吊着一张网床,不想爬了就躺在网床上摇啊摇,很自在。后来,因为要盖房子,那两棵五敛木被砍了。再后来,那两棵花桃木,随阿婆走后,也被砍了,盖上了房子。我刚上初中那会,离家住宿了,更少到阿婆家了,有一次我回来去阿婆家,阿婆给我拿了一袋花桃,原来是花桃木的花桃快熟的时候,阿婆摘下来,给我留着。花桃木隔离,还有一片鸡公花,长很高,夏天里开得很灿烂,我可以藏在里面玩,后来也没了。
花桃木还记得,有一次夏天的夜里,村里停电了,屋子里很热。阿婆把客厅扫干净,把凉席铺在地上,打开大门、小门还有窗,我们睡在厅里,比房间里凉快。那个时候,二舅家的房子在阿婆家房子对面,阿婆叫他的女儿、还有儿子过来一起睡,这里比较凉快,但是他们没有回应。阿婆等了一会,就没再等了。那个时候,不知道为什么,我感觉到阿婆很失落,明明那个时候的我,还不知道失落是什么意思。我想,阿婆是想他们来的,我也想他们来,这样阿婆就不会失落,会开心一点。那天晚上,阿婆手上的葵扇有一下没一下的在我身上动着,凉凉的。
在我二年级的时候,有一次我闹脾气,去了同学家里睡,没有和阿婆说,阿婆那天晚上找了我好一会吧,最后还是找到了,因为我同学的阿奶和我阿婆认识。那个时候我不是闹阿婆脾气,但是她来找我的时候,我闹她脾气了,*气说不回去,她没有办法,就留我在那,自己回去了。
后来三年级左右,我回家了,阿婆就自己一个人住了。我回家以后,每到过节需要祭拜的时候,我妈会让我走去阿婆家,帮阿婆做一些小工。那年春节,阿婆给压岁钱给我们,我发现我的红包里面是五块,二舅家的小孩的红包里是十块。那个时候,我不明白,都是阿婆孩子的孩子,为什么我的红包会比表妹表弟的少。所以有一次我妈让我去,我不想去,二舅的女儿比我小一岁,她家就在阿婆家对面,为什么我要去帮忙,她都不用做。还有我大姨家,也在村里,大姨的女儿年龄比我还大,为什么我要去帮忙,她们都不去。我变得很计较,但是我还是去了。阿婆总是一个人,还在老房子的时候,过节祭拜只需要烧一次鞭炮,搬了房子以后,在老房子拜完,还得到新房子那里拜一拜,烧一串鞭炮,响一响。后来,我认识到一个概念,外甥和孙子,我是阿婆女儿的女儿,是外甥,表妹表弟是阿婆儿子的小孩,是孙子。怪不得小的时候我去阿婆家,阿婆那边的邻居都打趣我说,外甥王又来了。
再后来,阿婆生病了,医院,去的第一天,我和表妹跟着去的,留在那里陪阿婆。阿婆所在的病房,有两个床位,阿婆一个,另一个床位也有一个老人家。我们到的时候,小舅跟我和表妹说,到傍晚的时候会来带我们回去。医院,去了一次就不想再去了,很害怕。快到傍晚的时候,小舅还没有来,我怕他忘记了,医院里陪阿婆过夜。幸好,他来了,带我们去吃饭,医院。我不想医院,但是我很害怕,如果我留下了,晚上就回不去了,所以我还是走了,还记得阿婆那个时候的样子,和那个停电的晚上一样。
最后,阿婆出院了,回家了,他们请了一个人在照顾阿婆,听我妈说,阿婆回来后,有一天精神比较好,走出市场大家都说她好了,但是没几天突然倒下了,没再起来,人们说那个是回光返照。我不懂,我没有见过。其实我现在都想不明白,为什么我不知道我没了阿婆,周末在学校回来的时候,什么都没了。我妈以前有时候会说,阿婆走的时候,化了一个很漂亮的妆。我不知道,我没有见过。我见过的阿婆,医院里。
我记忆里,阿婆总是自己一个人,阿婆有四个儿子,我都没有见过她和四个儿子在一起的样子,阿婆也有四个女儿,我也没见过她和四个女儿在一起的样子。记忆里,阿婆身边最多子女的时候,是有一次阿婆生日,应该是村里说的大寿吧,在二舅家摆了几台,大家一起吃饭,还有一个大蛋糕。但是我印象中的阿婆,没有坐在一起,是她自己一个人坐在厅里的木椅上,看着屋里一堆人。那天吃完饭,我还和表妹用零花钱,一起在市场地摊上买了一个小礼物,送过去的时候,那会阿婆已经在房里睡下了,不知道她是累了,还是开心。
再后来,我妈经常会说,要是阿婆再撑个十年,那个时候,阿公也走了,小舅也结婚了,大舅也回来了,日子就好过了。阿婆走后的十年,确实阿公也走了,小舅也结婚了,大舅也回来了。但是阿公还在的时候,阿婆也还是自己住,小舅结婚以后,阿公也还是自己住,大舅回来了也只是过年的时候在家几天。所以如果阿婆还在,我不知道对她来说,日子是好过了,还是重来了。
我忘了阿婆叫什么名字,以前她的邻居会叫她的名字,时间太久了,我忘了。我只记得,阿婆是我妈的母亲,她还有个双胞胎妹妹,和阿婆好像好像。
阿婆阿公走后,每年清明的时候,他们的生祭死祭的时候,祭拜他们的是阿公阿婆的儿子以及他们的老婆、子女。我不喜欢这样。
那些人清明回家的时候,我妈说全柳婆(我邻居,她的丈夫名字叫全柳)好不容易生病治好了可以下床走路了,但是前几天她家的人出去插秧了,中午还没有回来,她担心市场没菜买了,就自己骑单车去市场,回来以后,脚肿得很,又躺床上了。我很久没有见过她了,以前她常在傍晚的时候带着她的孙子散步来我家,我放假回家的话,她看到我会跟我说,又回来啦。有一次我放假回去,晚上只有我一个人在家看电视,她来我家,坐在木椅子上,和我说起了话。话里有村里哪个老人走了,哪个老人病了,其实她说的那些人我都不认识,只是她说着,我就简单应着。人老了,没用了,相近年纪的人都走了。
这次回家,在家门口见到另一个邻居,她问我还在广州读书吗?我说我已经毕业两年了,说了两次,第二次比第一次大声了点。她以为我还在读书呢。然后她问,在广州上班吗、做什么的、有多少钱。对于这个问题,我的回答还是那句,在广州搬砖的,刚刚可以养活自己。
以前我还在村里面的老房子没搬出来的时候,我妈说的早上把我放在隔离屋和那个老人一起煲粥,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,她拉着板车,从地里回来,在路上看到我,还和我打招呼,说我都长这么大了。我忘了怎么称呼她,只记得她矮矮的,说话带着点其他地方的口音,还有她家在哪,她家在我家老房子隔壁,但我没有回去过。
老房子那边,还有一个老人,自己一个人,我们叫他“阿爹”。早年间,我还看到他走在路上,他还来过我家,还钱给我妈。他有一个大哥,他大哥有老婆、有子女、有孙子外甥。我不明白,他一个人,可以到他大哥那里一起吃饭,只是多一双筷子。我妈说我不懂,我那个时候确实不懂,只是多一个人。现在懂了,但不想懂。
老房子那一片,真的有很多人,以前她们看到我,会说都长这么大了。她们记忆里的我,小时候没人管,像颗小石头一样,会动不动就哭,她们见到我会打趣两句,而我总是不能适应,不知道如何作答。我的更小时候的事情,都是在她们那听来的。
还有一个,我同学的阿奶,个子小小的,头发白白的,阿婆还在的时候,会去她家,或者她来阿婆家。年春节的时候,同学回来,我去那边烧烤,她阿奶还在。我记得初中毕业以后,我们到更远一点的地方上学了,变成了一个星期回一次家或者两个星期回一次家。我和我同学在同一个市里,不同一个学校。有几次我回家出市场的时候,她看到我,会跟我说,我同学没有回来,我不知道怎么应答,那个时候我和我同学很少联系了。只说可能她有事做吧。再后来,我同学结婚,我回去,她看到我,会说我同学和我读的学校不一样,说我有出息。其实都一样。
结尾小的时候,记得有一次我跟我妈去看别人打斋,那时候只觉得有趣,并不知道那个热闹好看的场面意义是什么。现在懂了,怕了。王晓燕小的时候,好像也跟着我妈去看过,还跟我说很好看,她和我以前一样,不懂,我没有和她说其他。有时候看着我妈和王晓燕她们,好像看到了阿婆和我,只是王晓燕她们比较幸运,她们的舅和姨会经常回家。
日子是过了就好,还是重来了,我不知道。
希望我写完了以后,不会再常常想起他们,我累了。
最后,祝大家年,健康平安,万事如意。
常怀感激之情,好好照顾自己,带着过去,奔赴将来。
帝里重清明,人心自愁丝。下一期再见,谢谢
END
一日平安一日福邮箱:qq.